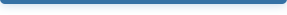在纸张出现之前,简牍是最主要的文字书写材料。《尚书·多士》里面记载周公对“商王士”的诰令,其中有大家熟悉的一句话“惟尔知,惟殷先人有册有典,殷革夏命。”这是说商人的先人已经有了简册,上面记载了“殷革夏命”的旧事。《论衡·量知》里记述了简册的制作方法:“截竹为筒,破以为牒,加笔墨之迹,乃成文字,大者为经,小者为传记。断木为椠,析之为版,刀加刮削,乃成奏牍。”简牍是对竹或木制成的书写材料的统称,包括简册、牍、觚等。可以说,竹木简牍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文字载体,承载着先人无穷的智慧。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:“天下之事,无大小皆决于上。上至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。”说的是天下所有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秦始皇来亲自裁决,甚至用“衡石”计算处理的文书,每天有明确的定额,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。“衡石”,张守节正义:“衡,秤衡也。”裴骃集解:“石,百二十斤。”秦代一斤的重量约合今天的250克左右,丘光明等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,得知其平均为257克(《中国历代度量衡考》,科学出版社,1992年,第394页),“百二十斤”约为30.8公斤,秦始皇每天必须处理的“书”据推算要超过30万字(王子今《秦始皇的阅读速度》,《博览群书》2008年第1期)。皇帝如此勤奋,地方官吏也是夙兴夜寐,不敢懈怠。
秦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,历史地位非常重要。可惜由于存在时间短暂且曾推行焚书政策,留下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。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牍,大约抄写于秦统一前后,包含20多种不同类型的文献,内容涉及古代政治、地理、社会经济、数学、历法、医学、文学、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,展示出当时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,使我们对战国晚期至秦代社会文化的了解大为丰富和扩展。从竹简《从政之经》之类的文献来看,这批简牍的主人应是秦的地方官吏。简牍入藏时原始保存状况较好,室内揭剥清理时发现简册还保存着成卷的状态,清理的10卷竹简下还留存有竹笥、椁板等承托物,可以推测简牍在最初装入竹笥时,就是分左右两部分层垒摆放的。这件竹笥,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位秦代官吏的“书箱”。通过“书箱”内的简牍,去了解当时“书”的内容聚合、简册序连和图书分类,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。
内容聚合比较好理解,就是把内容有关的文献编辑成一本书。韩巍先生曾经介绍过,在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牍中,与数学相关的内容比重最大,即卷三、卷四一部分与卷七《成田》、卷八《田书》,计有400余枚。抄写在卷四上的《算书》(甲种),共235枚简,其内容由四部分构成:
一是开头的32枚简,共800余字,以鲁久次和陈起二人问对的形式,通过陈起的回答,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、作用和意义。这段文字原无篇题,由篇首语定名为《鲁久次问数于陈起》。二是抄写于8枚简上的“九九术”乘法口诀表,分上下五栏,始于“九九八十一”,终于“一一而二”。三是《算书》甲种的主体,即“算题汇编”。其编排次序首先是“少广”术(简41-59);其后的简60-145分为“田”“租禾”“租枲”三篇,每篇之前各有一枚单独的“篇题简”;排在最后的简147至220,未见明确的篇题和分篇标志,但按《九章算术》分类,其排列顺序大致是“方田”“税田”“衰分”“粟米”“勾股”“合分、乘分”(《九章算术》归入“方田”)“商功”“赢不足”,与《九章算术》各章的排列顺序大多一致。四是衡制换算(简220-235),其单位从大到小依次为石、钧、斤、魁(六两)、两、锤(八铢)、锱(六铢)、分锤(四铢)、分锱(三铢)、铢(韩巍《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》,《文物》2012年第6期)。
这样,《算书》甲种的四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《鲁久次问数于陈起》相当于全书的“序言”,起到开宗明义的作用。该篇最后一句说:“郦(隶)首者筭之始也,少广者筭之市也,所求者无不有也。”有证据表明,“郦(隶)首”就是紧随其后的“九九”乘法口诀表的别名(韩巍《北大藏秦简〈鲁久次问数于陈起〉初读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3期;程少轩《也谈“隶首”为“九九表”专名》,《探寻中华文化的基因二》,商务印书馆,2018年,第202页)。而“九九”乘法表之后,位于“算题汇编”之首的恰恰是“少广”。由此可见,《算书》甲种的篇章结构是编者精心安排的结果,体现的是数学文献同类聚合的态势。
一种数学“书”需要235枚简抄写,若是勤加翻阅,“韦编三绝”的故事恐怕也不会少。散乱的竹简就要重新编序,初次抄写完成的竹简同样也会有编序的问题。“简背划线”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发明。在北大秦简牍整理过程中,孙沛阳发现了“简背划线”的存在。随着整理的深入,研究者发现参照背划线来重新恢复简册也并非那么简单。
背划线以刻线最常见,墨线情况较少。绝大部分都是自左起,向右下斜行,形成于编联之前,目的是为竹简标示次序,最终为编联成册做准备。从已有资料看,面向简背时,背划线都是自左起,向右下斜行,即左高右低。但从战国、秦到西汉简,背划线划过的简数(或者说背划线的起止长度)不太一样。但是在一篇之内,似乎各组背划线划过的简数还是基本相同或接近的,这说明书手在抄写这一篇时,取用的是同一类竹简,它们可能就是同一个制简人制作的同一批简。背划线制作的目的是对竹简的顺序进行标示。这种标示是对书写文字之前的竹简所作的一种初始序连(何晋《浅议简册制度中的“序连”——以出土战国秦汉简为例》,《简帛》第8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年,第451-469页)
那么,书手在抄写中取用这些竹简时可能完全遵守这种初始序连,也可能有时不太那么严格遵守。编联成册是最终的序连,此时无论是竹简的物理顺序还是文字内容顺序都被彻底固定下来。这时我们可以观察,初始序连的背划线和最终序连的文字内容顺序之间的对应关系。如《田书》的背划线,按照正面文字内容的成田亩数,一亩、两亩依次排序时,理论上简背面的背划线应该是一条左高右低的斜直线,实际的情况却呈现出不规则“W”形的曲线。这是由于书手在取简时弄错了上下方向,或竹简背面划上划线后并未翻过来,书写者取用时可能从右到左把简翻过来一支书写一支,这两种情况都可能造成“逆次简册背划线”。
《田书》的成田亩数等数字内容是规律化的,假如卷八整理时已被扰乱,并未像现在一样留下较为清晰的分卷情况,简背划线即成为重要的参考,则不可避免地与简文内容产生令整理者苦恼的抵牾。这提醒我们在简册序连时要对简背划线的作用保留清醒认知。背划线在编连中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分组,而在一组内它又可部分起到简单页码的作用(或由于书手疏忽,前后页码会出现颠倒),而各组的先后顺序,并不能通过划线确定。
“书”在竹简上抄写完毕,不阅读时可能会被放入书箱。书箱里不同种类的书是怎么摆放的,也是有趣的问题。前面也提到,秦简牍在最初装入书箱时,是分左右两部分层垒摆放的,也即室内发掘固定后的东、西两组。东组的主体卷三、卷四为算数书。西组卷〇《三十一年质日》、卷七《成田》、卷八《田书》与卷五《三十三年质日》放置于一处。“质日”简,是秦汉官吏所使用的一种值班日历或值班日记,罗振玉、王国维等原称其为“历谱”,马克曾改称为“历日”,以为它相当于后世历书。若将其视作古书,还是应当归入《汉书·艺文志》(简称《汉志》)所记述的“历谱类”(李零《兰台万卷:〈读汉书·艺文志〉(修订版)》,北京:三联书店,2013年,第182页)。
巧合的是,“历谱类”在《汉志》中归入《数术略》。《汉志·数术略》共计载有18种历谱书,其中有算术书两种,即《许商算术》26卷、《杜忠算术》16卷。这两种书与东汉时期的《九章算术》有关是学界共识。如顾实“盖其书(《许商算术》)与今存《九章算术》有关”(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224-225页)。沈钦韩也认为“此许商、杜忠所为即是九章术。(《汉书艺文志疏证》,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145-147页)。”钱宝琮也指出“(二书)应该是东汉初编纂的《九章算术》的前身。(《算经十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3年,第83-87页)。”几篇竹、木觚、牍的“佣作文书”也是与同类文献相邻。卷四下竹牍Z-011,《田书》下木牍M-016与木觚M-015等,均是雇佣劳作及支取工钱的记录。
另外,卷一《公子从军》、卷九《从政之经》《教女》、木牍M-009《泰原有死者》及木简乙《隐书》等五篇归属《汉志·诗赋略》杂赋类的文献,它们的位置关系是《泰原有死者》在最上,下面叠压《公子从军》,《公子从军》与《从政之经》《教女》可依次提取,《隐书》叠压在卷九之下。两篇诗赋略·歌诗类文献,木牍M-026“歌诗”整齐地压在竹牍Z-002“歌诗”之上。这就说明书箱内不同种类的“书”可能是按类别分开放置的。
综上所述,透过秦代基层官吏的书箱,不仅使今人看到了秦代图书文献分类、聚合的实物证据,也提示着《汉志》及由其上溯的《别录》《七略》等文献分类方法并非空中楼阁,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渊源。
(作者:杨博,系维多利亚vic登录地址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)